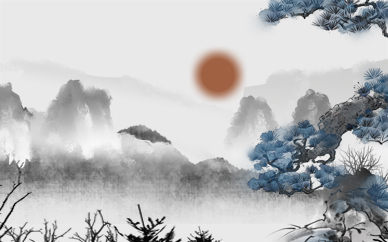初冬子夜,辦公樓的燈光漸次熄滅。街道空寂,路燈的光暈薄薄地敷在柏油路上,托著梧桐疏落的影子。拐過街角,一團暖光忽然撞入眼簾。
還是那輛鐵皮餐車。走近,要了一籠包子、一碗餛飩。等待的間隙,細細打量著它。這是輛三輪車改造的餐車,粗糙而實用。車頭的擋泥板銹出深褐的云紋,扶手的套膠早已磨光,露出里面的鋼管,被反復摩挲得發亮。車座的人造革裂開細密的口子,翻卷處露出灰黃的海綿,坐墊中間卻磨出油亮的暗色——那是經年累月的體溫與重量的烙印。
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車身上架著自制的長方形鐵皮餐臺。臺面嵌著三口鍋:一口熬著濃白的豬骨湯,湯面凝著薄薄的油膜,一口滾水翻騰,專候餛飩下鍋,還有一口冒著綿密的白汽,層層蒸籠疊得老高。爐灶是舊式煤氣罐,開關擰動時,總先“咝”地輕嘆一聲,隨即藍黃的火苗驀然躍起,歡騰地舐著鍋底,湯鍋很快“咕嘟”起來。
餐臺上方支著雨棚,四根竹竿被鐵絲綁在臺角。棚下懸一盞老式白熾燈,燈下墜一小木板,上書紅色“餛飩·小籠包”字樣。車旁擺著兩張折疊小桌,其中一張的桌腿下墊著半塊碎磚——磚塊已深深嵌入地面,仿佛天生就該在那里。
男人的圍裙已洗得發白,袖口挽到小臂,沾著星點面粉,領口的扣子卻扣得嚴謹,一絲不茍。他抓起一把餛飩撒進滾水。餛飩是女人現包的,皮薄如紙,透出里頭櫻桃大小的粉色肉餡。
“餛飩,多加香菜,不要紫菜。”我說。
“好嘞。”男人應聲掀開鋁蓋。一團白汽騰起,瞬間將他籠罩,又漫溢開來,溫暖了清冷的夜。女人拿起碗,輕聲問:“要辣子不?”我點頭。她舀起一小勺辣油,油色紅亮,在湯面徐徐漾開。
問男人怎么還不收攤,他看向路燈延伸的遠方:“再等等,到兩點了再收,加班的、趕路的還不少呢。”
正要告辭,一輛路過的黑色小轎車忽然停下。司機搖下車窗:“老樣子,兩份餛飩、兩籠包子,帶走。”男人應著,女人已動起來。打火、燒水、包餛飩……爐火重燃的剎那,那團暖光似乎更亮了些。
我起身離開。走出不遠回頭望去,餐車漸漸隱入夜色,那對夫婦的身影在光暈里模糊成溫暖的剪影,男人正在收拾碗筷,女人擦拭著小桌——她擦得很慢,很仔細,像在撫摸孩子的脊背。
風依舊涼。但喉間那口湯的暖意,卻順著經絡慢慢洇開。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25年12月17日 20 版)